晋商没落,徽商崛起
盐商在明朝末年分为晋商和徽商两大集团,在全国各主要贸易城市兴建作为商会办公场所的会馆( 如山西会馆、徽州会馆、新安会馆等),与官府保持密切的联络,都是组织严密的商会。其中晋商兴起较早,实力也较强。清初,康熙皇帝击败准噶尔可汗噶尔丹,统一大漠南北,又取得雅克萨战役的胜利,迫使沙俄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,北方从此安宁。在这些战争中,晋商向清军提供了大量粮食和食盐等物资,出力甚多,名利双收,一时风光无二。然而自此以后,情况却急转直下,晋商逐渐没落,徽商则突然崛起,成为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等皇帝的宠儿。究其原因,主要有两点:
一、晋商文化较为保守,晋商在外出差时不许携带家眷,不许在山西以外购置房产,务求落叶归根;徽商则截然相反,可以携带家眷长期在外地居住,在外地购置房产无限制,几十年不回故乡也习以为常。徽商的主要居住地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北岸的扬州,由于清朝初年的“扬州十日”消灭了大部分扬州本地居民,此后大批徽商携家带口涌入扬州,很快反客为主,扬州的口音、风俗都接近安徽,被称为“徽商殖民地”。除了经营合法盐引贸易的徽商大批定居扬州之外,从事食盐走私贸易的徽商则主要定居在扬州西侧的仪征,他们表面上与合法徽商相互竞争,实际上经常串联一气,保证了整个徽商集团的稳定收入。
二、康熙帝平定北方之后,北方驻军大量减少,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又时开时闭,晋商的市场逐渐萎缩。华东和华南则事务繁多,经济也不断发展,清朝的各类资源向东南集中,使徽商的市场日益扩大。康熙帝与乾隆帝都六下江南,可见江淮地区对清朝经济的重要性。
虽然康熙帝与乾隆帝分别六下江南,但其支出来源却有区别。清朝与以往中国各朝不同,在户部之外,另设有一个财政中心——内务府,专管皇室财政。内务府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一些经济部门,如安徽的两淮盐政、江苏的江宁织造、苏州织造、浙江的杭州织造、广东的粤海关,都长期由内务府旗人把持,负责给清朝皇室敛财。康熙帝下江南时,主要负责接待的便是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、苏州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李煦、曾任粤海关监督的杭州织造孙文成,合称“江南三织造”。这三人均为内务府旗人,而且曹寅是李煦的妹夫,曹寅与孙文成又是儿女亲家。
康熙帝六下江南,虽然花钱如流水,却没有引发政府官员的大规模抗议,主要原因是他六下江南用的是“江南三织造”代表的内务府财产,不需要户部报销,正如《红楼梦》所说,是“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”,不属于“公款旅游”,而属于“自费旅游”。然而,为了有钱接待康熙帝一行,“江南三织造”疯狂地压榨丝商和盐商,因此在康熙时期,徽商大多生计艰难,罕有巨富。不过,他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
徽商创造“官商互动文化”
康熙帝驾崩时,“江南三织造”把宝押在八皇子胤禩身上,不料胤禩在皇储竞争中失败,给他们招来大祸,很快就都被新登基的雍正皇帝革职抄家。雍正皇帝借机整肃官场,此后,两淮盐政和江南三织造变得“清廉”许多,对丝商和盐商的压榨也轻了许多。于是,从雍正中叶开始,徽商变得日益富有。当乾隆皇帝打算下江南时,他深知两淮盐政和江南三织造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接待自己,又不能从户部拨款“公费旅游”,因此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富有的徽商。
乾隆年间的徽商领袖,是两淮盐业总商江春。江家从雍正年间起控制着十分之一的淮盐,江春本人担任两淮盐业总商达52 年之久,积累起巨大的财富,乾隆帝六下江南,都由江春组织接待。像康熙年间的曹頫、李煦、孙文成等“江南三织造”一样,江春为乾隆皇帝在华东修建了一系列行宫,还三次入京为皇太后祝寿,并多次向朝廷捐款,总数高达1120 万两白银之巨。乾隆皇帝也厚待江春,多次去其家中拜访,甚至于称兄道弟,江春号称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。商人直接与皇帝打交道,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一时间,各级官员无不仿效乾隆皇帝,江春府上门庭若市,俨然与总督、巡抚平起平坐。为了发展与乾隆皇帝的私人关系,并令来家中拜访的各级官员称心如意,江春还精心设计了大量的文化娱乐活动。
现代中国人所谓的“传统文化”,例如饮食、收藏、风水、文艺等等,其实大多在清代才算定型。两淮盐业总商江春,正是塑造清代文化的核心人物之一。以江春为代表的徽商身为盐商,很容易获得大量的调料,其中一些更是明朝之前尚未引入中国的(例如辣椒),在研究饮食文化方面可谓得天独厚。为了迎合皇帝和官员,他们发明了众多精美的菜肴,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食谱,所以很多中国名菜都与清朝君臣(特别是曾经多次下江南的康熙、乾隆) 有关。在这一时期,宋朝才发明出的炒菜突飞猛进,一举成为中国的主要烹饪方式,中国自古以来流行的分餐制也被合餐制取代。炒菜与合餐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餐,使中餐同世界上其他的菜系有了本质区别。
炒菜的流行,是因为炒菜味道浓烈、口感脆嫩、烹饪时间短,适于接待官员,至于耗油多不多、油烟大不大都无所谓( 食用油在古代非常昂贵,因此炒菜在清朝以前一直流行不起来) ;合餐制的流行,则使用餐时间变得更长,有利于发展用餐者之间的关系,宾主之间的互动更多,是否卫生也无所谓。
究其原因,在乾隆年间,徽商要利用“淮扬菜”将中国的官商关系推向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,为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。由于清朝官员的流动性极大,经常在一个省才上任几个月,就被调到另一个省,徽商创造的“官商互动文化”也随着清朝官员的调动而迅速扩大影响力。很快,在“淮扬菜”的带动下,中国各大菜系都向精细化、炒菜与合餐制方向发展。到了清朝末年,现代人熟悉的中餐最终定型,而徽商实为现代中餐的奠基人。
在徽商的介绍下,华东的园林建筑、风水文化也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,北京和承德等地的园林如圆明园、颐和园、恭王府、避暑山庄等,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华东园林的“山寨版本”。为了避免直接行贿,徽商热衷于“雅贿”,将他们重金收藏的古玩字画送给皇帝和达官贵人,不断在中国掀起“收藏热”。
改造中国戏曲表演
徽商对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贡献,是对中国戏曲表演文化的改造。江春生前很喜欢戏曲,也需要用戏曲娱乐来访的皇帝和官员,因此对优秀的戏曲艺人十分慷慨,“演出一戏,赠以千金”。在以江春为首的徽商重金诱惑下,全国各地的戏曲艺人纷纷涌入扬州,为盐商效劳,故而有“商路即是戏路”的说法。这些外来的戏曲与江苏本地的昆曲在扬州相互切磋提高,扬州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中心。耳濡目染,许多在扬州定居的安徽人都能表演多个地方的戏曲,号称“徽班”。南巡期间,乾隆皇帝也喜欢上了徽班的表演。为了祝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,江春临终前派四大徽班进京,广受北京官民欢迎,迅速压倒了此前在北京流行的秦腔,于是扎根北京,形成了现在的京剧。
纵观人类历史,很少有哪个人能够产生像江春这么大的文化影响。江春热衷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,并不是因为他无比热爱文化,而是为了巴结皇帝和高官,以便谋取私利,特别是方便让自己的家人做官。说到底,江春研究的文化,都是腐败文化。在内心深处,他和其他徽商一样,并不认为盐业贸易是个值得骄傲的职业,急于想方设法摆脱资产阶级的身份,加入地主阶级。在这方面,徽商们的思想与欧洲的美第奇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如出一辙。在清朝这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中,他们只不过是地主阶级谋利的工具,自身既不具备反抗意识,又缺乏军事力量,无法避免悲惨的结局。江春死后,江家由于同和珅的关系过于亲密,招致嘉庆皇帝的反感,失去了两淮盐业总商的职务,又无法在清朝官场上立足,生计窘迫,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,落得和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一样的命运。不过,这并未阻止其他徽商继续沿着江春探索出的官商勾结之路前进。
有会馆的地方就有商会
在晋商、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的示范作用下,在清朝中期,中国商业日益繁荣,商人大批旅居各商贸中心城镇,催生了一种建筑类型的崛起——会馆。
会馆起源于先秦的驿馆,最早的功能只是旅店。自北魏开始,出现了多功能的驿馆,一些商人直接在驿馆里做生意,隋朝发明科举制度之后,京城的驿馆又时常成为赴京赶考的各地学子进行考前培训的场所。“会馆”之名始于明代,清朝初年“湖广填四川”,大量外地人涌入四川,一时没有足够的住宅供他们居住,导致驿馆疯狂扩张,形成了多处巨型“会馆”。此后,随着清朝商业的发展,全国各地会馆林立,以北京、江苏和四川为最多。这些会馆大都以地域划分,是某地移民在特定城市的宗教、文化、经贸、社交中心,堪称“微缩殖民地”。尽管具备多种功能,但纵观各地会馆,其最常见的功能依然是商业,会馆通常还会向属于该籍贯的移民定期索要会费。
中国的会馆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建筑。在除北京之外的城市,会馆通常都是当地最豪华气派的建筑,不受风水理论的约束,特别是门楼造型极为夸张,彰显强大的财力与社会影响力。北京的会馆多为在京官员离职后捐给同乡会的故居,外观较为朴素,内部却相当讲究。北京商人坐守皇城,安土重迁,极少出京做买卖,因此中国各地都没有“北京会馆”。广东受益于清朝中前期广州“一口通商”的外贸政策,经济繁荣,广东商人在全国各地兴建了上百家会馆,但广州城内却连一家外省会馆都没有。这是因为清朝广东社会地域特色鲜明,外省商人极少有在广东经商成功者,即便福建、浙江等临近省份的商人来广东,也往往要冒充成广东人失散多年的亲戚,拜了码头,才能在当地立足,广州可考的外地会馆只有同属广东省的潮州会馆一家而已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广州城南林立的外国商馆,例如为西洋各国建造的“广东十三行”夷馆,以及越南会馆等。会馆的分布和格局,很好地体现出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特点。
可以说,中国有会馆的地方,就有商会。然而,以商会的标准来衡量,明清时期的中国会馆大都显得不够“专业”。尽管拥有了商会的各项功能,多数中国古代会馆的本质依然是排斥其他省份商人的同乡会。由于中国的地域差别极大,同乡会有很强的生命力,其影响力至今不衰。然而,这些传统社会组织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却暴露出许多弊端,一筹莫展。
中世纪商会走到了尽头
鸦片战争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,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商业。1842 年,英军逼近扬州,索走50 万两白银赎城费,清政府又因势利导,诱使英军血洗仪征,杀死两千余名私盐商贩,焚毁盐船数百艘,徽商损失惨重。随着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开关,盐价暴跌,盐商的吸引力荡然无存,以胡雪岩为代表的清末徽商只得转而开辟其他商业领域,虽然获得过一些成功,但在洋货的冲击浪潮下,最终大多归于失败。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清末晋商一度因中俄贸易发展,靠向沙俄出口茶叶和开展金融业务而中兴,但自十月革命之后便一蹶不振。而在香港、上海、天津等被西方列强控制的地区,则相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近现代专业商会,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,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地域界限,以职业作为入会的主要标准,适应了时代潮流。中国中世纪商会,至此走到了尽头。
中国历史上盛产江春、胡雪岩和乔致庸这样的商人,无论他们生前多么富有,都从未有过发动资产阶级革命,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念头。正相反,通过官商勾结,这些“红顶商人”们用各种行贿方式向地主阶级输送利益,反而加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。真正有希望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国商人,是蒲寿庚、王直、郑芝龙等涉嫌非法经营、亦商亦盗的商人,他们与欧洲资产阶级有着很大的相似性,也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,敢于同中国朝廷一较高下。只有这种人夺取政权,中国才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。然而,他们最终都失败了,在地主阶级的史书上沦为不光彩的丑角。于是,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工业强国“坚船利炮”的牺牲品,带着巨大的羞辱和阵痛进入近代世界。


 进一步激发境外旅客入境旅游消费活力离
进一步激发境外旅客入境旅游消费活力离 当律师遇上AI,会擦出怎样的火花
当律师遇上AI,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经济政策一线微观察丨保障公平竞争 激发
经济政策一线微观察丨保障公平竞争 激发 圣境甘南:从草原到山城的县域振兴实践
圣境甘南:从草原到山城的县域振兴实践 防飞絮闹春扰人 黑科技轮番上阵
防飞絮闹春扰人 黑科技轮番上阵 党建聚力谋共富 春日派对展新颜——杭州
党建聚力谋共富 春日派对展新颜——杭州 中国经济样本观察·“镇”了不起丨20亿
中国经济样本观察·“镇”了不起丨20亿 经济大省挑大梁|潮涌南海勇向前——广
经济大省挑大梁|潮涌南海勇向前——广 盐都富顺 梦里水乡
盐都富顺 梦里水乡 “一针一线”织就创新引领的担当和勇气
“一针一线”织就创新引领的担当和勇气 《求是》杂志刊发中共全国工商联党组署
《求是》杂志刊发中共全国工商联党组署 两会聚焦|争做创新主体,构筑竞争优势
两会聚焦|争做创新主体,构筑竞争优势 沈莹出席广东省民营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
沈莹出席广东省民营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 全国工商联与中国建设银行召开2025年推
全国工商联与中国建设银行召开2025年推 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管理改革工作会议
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管理改革工作会议 团九江市委书记周丽敏一行到访中青企协
团九江市委书记周丽敏一行到访中青企协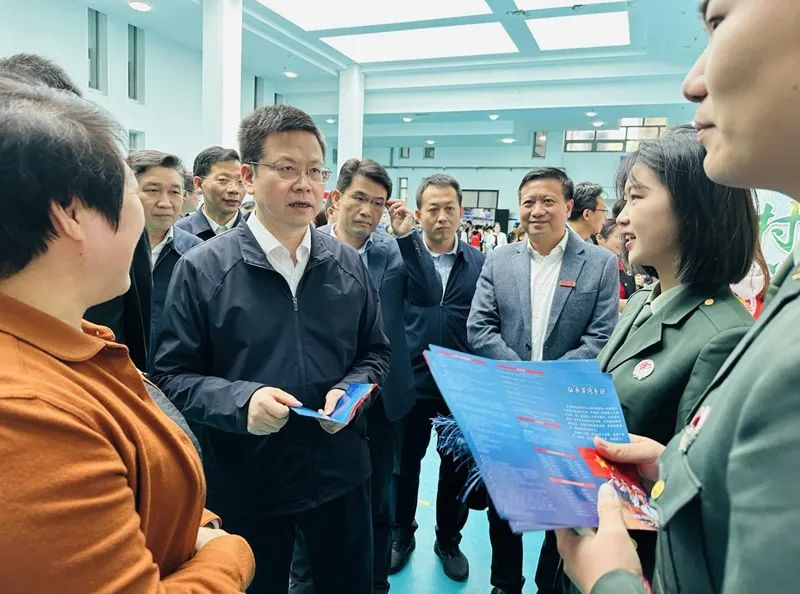 2023“百城万企”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
2023“百城万企”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支部赴李大钊故居
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支部赴李大钊故居